|
影视投资 https://www.touzitop.com/ 本月开始,大碗将用长达一年的时间,推出一个新的系列专栏:“大碗看江浙”。 江浙的各个地市,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,民营经济的桥头堡,共同富裕的示范田,同时也是房价最高的旗手之一…… 进入这些城市,打开他们的经济图卷,我们所看到的是——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楼市30年的浮沉。 上周,我们去了“大碗看江浙”的第一站:温州。 行走其中,感受着改革开放40年的大历史在温州碾过的痕迹,我心中充满唏嘘。 35年前的温州,是那样的耀眼。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、珠江模式,如三叉戟一般,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犁出璀璨的改革火花。 20年前的温州,是那样的激昂。 头顶着“大胆试验、中央支持”的试验区光环,淋漓尽致的展现着“勇于突破,敢为人先”的温州精神,与苏州和东莞一起站在高台上。 10年前的温州,是那样的亢奋。 最高地价3.7万/㎡,最高房价10万/㎡,10万温州人从鄂尔多斯炒到海南。中国大地上,“温州炒房团”万里颂扬。 今天的温州,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? 12个区县,半数人口流出。人均GDP,滑脱到浙江全省倒数第三。在共同富裕示范区里,成为浙江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。 最高房价,从10万/㎡跌回了4.5万/㎡。楼市兜兜转转10年,又回到了原点。 曾一起站在高台上的东莞和苏州,如今但凡正眼看一眼温州,就算我输。 用20年时间,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。 温州,怎么了? 仅仅是因为温州人爱炒房、爱上杠杆、爱投机? 1985年,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—— 《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》。 这篇头版文章中,讲到一句话:乡镇工业看苏南,家庭工业看浙南。 千万别小瞧这句话,这是“温州模式”第一次得到官方层面的肯定,与苏南模式站在了一起。 温州人等这句肯定,等了7年。 七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,高层确定了改革方针。 一大批头脑活络的温州人,全家出动,在自家的作坊里生产出一批批的螺丝、纽扣、线圈等针头线脑小商品。 这些小商品,被上万名的温州供销大军带着,投放到祖国大江南北。 当年的中国,物资奇缺。 小商品的“流通差”,成为了温州人的第一桶金。 第一桶金上,诞生了中国最牛的一批乡镇企业家。最牛批的,当属“温州八大王”— 五金大王胡金林、矿灯大王程步青、螺丝大王刘大源、合同大王李方平、旧货大王王迈仟、目录大王叶建华、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中。 八大王之下,是更多的温州人扔下“七山一水两分田”的两分田,一头扎进了开厂倒货的私营事业里。 好日子刚过了四年,坏消息来了。 1982年,高层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,开刀“投机倒把”。 温州八大王被抓了,其他个体户跑路了……短短两年,温州工业增速从31%跌到-1.7%。 这是温州历史上的第一次跑路潮。 直至1985年,温州人等到了解放日报的头版文章,也等到了八大王被平反释放。 更等到了,最高层的批示—— 温州作为示范区,要“大胆试验、中央支持”。 有了政策支持,那就撅起屁股开干吧。 此后15年,温州人塑造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—— 小小温州,产生了桥头纽扣市场、乐清五金电器市场、虹桥农贸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。这十大专业市场的背后,是几千个生产基地、十万个家庭作坊、数以万计“小商品”和千军万马供销军。 温州跺跺脚,中国小商品市场抖三抖。 ▲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作坊里,敲出了温州奇迹 赚到钱的农民想进城,没有城镇户口,又进不了城。于是,苍南县的宜山、钱库、金乡等地的农民,来到小渔村龙港,自己掏钱,买地施工,“造”出来一座城:龙港。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靠农民集资建起来的城市。 ▲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挂牌 做生意,要用钱。但银行贷款难度大,流程长。于是,温州人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“方兴钱庄”和第一家民间股份银行“鹿城城市信用社”。 这是中国民间金融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。 ▲方兴钱庄,开业第二天被国有银行抵制,转入地下 在外地的供销铁军,逢年过节要回温州。没有航班,那就买飞机、开辟航线。 最终,温州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私营包机公司“天龙包机业务公司”。这家公司,也是吉祥航空的前身。 这是中国民营航空迈出的第一步。 ▲龙港镇举行建镇10周年,温商王均瑶包飞机撒彩带庆祝 温州的经济奇迹,与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 它一不靠政策,二不靠补贴,三不靠特区。 靠的是一个个家庭作坊,一个个供销铁人,一个个敢打敢拼的温州普通人…… 2000年,英国BBC做了一档纪录片《通往富裕之路》。 他们来到中国采访,想要告诉全球: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,即将给世界带来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。 BBC进入中国的镜头,只投射在了两个地方: 一个是上海,这是世界眼中的中国城市。 另一个是温州,这是世界眼中的中国乡镇。 也就是在这一年—— 温州的经济总量,从13亿跃升到822亿。排名浙江第三,仅比宁波低了354亿。 同一年,东莞的经济总量是489亿,仅为温州的59%。 而20年后,东莞是温州的1.4倍,宁波则是温州的接近2倍。 今天的温州,似乎再也回不去BBC镜头下的那个年代了。 2001年,温州迎来了第一波的关停潮。 关停的企业,大都是打火机公司。 造成这波关停潮的原因,非常小—— 1994年,美国针对中国的打火机企业实行了CR法规。 该法规以保护儿童安全为理由,要求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,必须加装安全锁。紧接着,欧盟也通过了CR法规。 之后,温州的“打火机一条街”信河街,每天都有企业关停。 短短两年时间,温州的3000家打火机公司,只剩下不足300家。 这波关停潮,只是温州企业的一个缩影。此后十年,同样的戏码,屡次上演。 前文我们讲到过—— 温州奇迹的背后,是商品奇缺年代里的“流通差”。 别人不敢干的,我敢干,我先干。 于是,温州就在商品奇缺的年代里,依靠敢为人先的家庭作坊,圈地为王。 于是,温州就在出口放开的年代里,依靠价格低廉的针头线脑,抢占市场。 10年之后,伴随东南亚市场的崛起以及国家对民企准入的进一步放开—— 你敢干的,我也能干了。 你便宜,我比你更便宜。 温州原有的“流通差”和“制度差”,消失了。 此时的温州,面临着两条路—— 产业升级,进入更高的行业,攫取更高利润。管理升级,整合家庭作坊,以规模降低成本。 但是,这两条路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—— 来钱儿太慢! 脑筋活络的温州人,很快发现了第三条路:投资,或者叫炒。 2001年的夏天,温州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上,坐着157名乘客。这群人,是《温州晚报》所组织的看房团。 他们在上海呆了三天,5000万,买下100多套房源。 一个月后,一列列的专车将一批批的温州人投放到了上海楼市,乐清帮来了, 瑞安帮来了,企业老板来了,公务员来了,普通人也来了…… 成交金额,也屡创新高。5000万、6800万、8000万、1.8亿…… ▲当年举着牌子走下飞机的人,是否撑过了2011 一年后,上海申博成功,新天地开业,恒隆广场开业,陆家嘴滨江商业开业,地悬浮列车通车,地铁2号线通车。 浦东的房价,从3600元/㎡跳涨到4700元/㎡。 温州购房团的年化收益,干到了50%,甚至是100%。 2001-2002年,一批批的温州购房团奔赴上海。他们把原本用于扩大生产和购买原材料的资金,以上亿的规模砸在了楼市上,并攫取了远超出预期的收益。 这一年,对于数以万计的温州人来说,是值得纪念的一年。 潘多拉魔盒,打开了盖子。 他们知道,实业的路,再也回不去了。 2002年之后,尝到甜头的温州购房团,开始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,就像10年前他们奔赴全国,销售针头线脑那样。 从哈尔滨到三亚,从重庆到上海…… 10年前的温州人,把针头线脑带到全国,把钱带回温州。 10年后的温州人,把钱带到全国,把房产证带回温州。 2000年之后的温州人,不仅把目光聚焦到了房产,还聚焦到了除实业之外的几乎所有领域。 大蒜、生姜、煤炭、能源、螺纹钢…… 从能源到房产,从衣食行住到有色金属,全被温州人炒了个遍。 2000年开始,煤炭价格大涨。 温州400户家庭带着30多亿现金,奔赴山西。他们在山西,承包了300多个中小煤矿。 2004年以前,温州人承包了整个山西90%的小型煤矿。 你以为,温州人买矿是为了挖矿炒煤? 不,你还是太年轻。 温州人买矿,纯粹为了炒。 三五个人筹钱,再上2倍杠杆,一口气吃下县城的绝大多数小型煤矿,便于控盘。 然后,坐等煤价上涨,等人接盘,集中转手卖掉。 这种操作,熟悉不? 是不是,有点像现在的炒学区和炒二手房—— 集资筹钱,吃下一个小区的二手,集中控盘;坐等涨价,拉起来之后,集中脱手。 对! 现在用于炒学区的狗屁黑科技,10年前就已经被温州人拿来炒煤矿了。 在炒房和炒煤炭之间,还有一批温州人发现了更快的来钱方法—— 炒钱! 自改革开放以来,温州一直都是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区。 最早期的温州民间资本,玩的是“呈会”。 10个亲朋好友,成立一个互助基金会。每个人出1万块钱,10个人就是10万。这10万块钱,在10个人中轮流存储。拿钱的人,给其他成员支付利息。 月息,大致为1%。 此时的呈会,还有互帮互助的“结义”味道。 慢慢的“呈会”变性了,结出了更大的怪胎—— 呈会的借贷,不在局限于小圈子,而是面向公众存贷。甚至,还出现了小会套大会的层层嵌套。 月息也不再是1%,高达6%、12%、40%。 当年结义的呈会,变成了高利贷性质的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。 最高峰时期,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达到了3000亿,利息达到惊人的15%以上。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,温州大地上,奔流着三股浪潮—— 左边那支,是以房产核心的实物资产。 右边那支,是以煤炭为代表的大宗商品。 实物资产和大宗商品之下,涌动的是活跃蓬勃但危机重重的高息民间借贷。 这三股浪潮,在2008年相遇了,冲刷出更大的泡沫。 2008年,美国次贷危机爆发。 中国为了对冲危机,财政部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政策,央行5次降息3次降 准。 民间资本最活跃、投机情绪最浓重的温州,遇上了史上最宽松的财政政策和最汹涌的货币放水。 温州,陷入了一个更大的怪圈。 一边是,普通人从银行低息套钱,放入民间借贷,吃进利差。另一边是,开发商从民间高息借钱,高价拍地。 高额利息,让购房者产生了虚妄的购买能力,咔咔买房。 高涨房价,让开发商产生了虚妄的偿还能力,借钱圈地。 2008年,温州绿城鹿城广场开盘,最高房价卖到了4.5万/㎡,是上海的2倍。 2010年,原温师院操场地块开拍,楼面价拍到了3.7万/㎡,是杭州的2倍。 高涨的投机情绪,穿过汹涌的民间资本,照射在乘风破浪的楼市大船上。 这是属于温州最后的时代高光。 2011年前后,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,成为中国的第一代街头网红。 中国大地街头巷尾的地摊上,都能听到这样的广告词—— 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!老板黄鹤吃喝嫖赌,欠下了3.5个亿,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…… 黄鹤的背后,是一代温商的垮塌。 2010-2011年,全国“金融去杠杆”,遇上了全国“楼市大调控”。 楼市收紧,连续出台3轮集中调控。央行连续5次加息,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。 此时的温州民间借贷,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。月息达到6分,年化最高达到150%。 此时的温州房价,泡沫也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。人均收入3万的温州,地价干到了将近4万。 该来的,终于来了—— 温州爆发了规模最大的民间借贷危机,跑路潮来了。 江南皮革厂黄鹤因赌债跑路;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跑路;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资金链断裂失踪;百乐家电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抓捕归案…… 仅9月12日至22日,10天时间有7家温州知名企业的老板,卷入失踪漩涡。 一个个单一事件,成为一桶桶燃油,倒入了民间借贷危机的火坑中。 火势,已蔓延至温州全城。 温州地区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5%,远超平均1.5%的水平。部分银行的坏账率,高达20%。 此时的温州,已经无人能救。 温州楼市和金融市场,在沉默的放弃声中,硬着陆了。 温州银行业,统计亏损金额达到1600亿元,而民间信贷亏损额也高达百亿元。 温州房价全面腰斩,集中坑杀。鹿城广场从10万/㎡跌回到了开盘价4.5万/㎡。 爆发危机,本不可悲。 可悲的是—— 危机爆发后,银行的一系列骚操作,更让温州人绝了实业的心。 据不完全统计,温州有98%的企业存在互保贷款。 在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,诸多银行秉承着“死道友不死贫道”、“情况不对拍屁股就跑”、“只同甘不共苦”的精神—— 他们在一家企业发生危机后,对互保企业立即抽贷。 2008年逼着你去借钱的银行,2010年全在逼着你还钱。 于是—— 温州一大票运行良好的企业,因为互保联保,一夜之间锅从天降,被拖入泥潭中。 2012年,拥有90多家子公司的庄吉集团,因银行连续抽贷和船东弃船,陷入了资金困局。 为之提供担保的众多民营企业,担保总金额逾300亿元,受到牵连,遭到银行断贷。 温州商界,每天都能听到跳楼、跑路的消息—— 借钱的老板,互保的企业、倒钱的中介、出钱的普通人,人人自危。 哪怕是10年后的今天,温州人再提到那场危机,仍噤若寒蝉。 他们在实业中受过的伤,倒逼着他们以更快的速度倒入一场场更大的危机中。 2013年,P2P席卷大江南北。 温州人一看,屁的P2P,不就是咱们30年前玩烂的“抬会”。 走,去互联网之都杭州,搞起来。 2015年,区块链席卷大江南北。 温州人一看,屁的数字币,不就是咱们20年前玩烂的“集资传销”。 走,去互联网之都杭州,搞起来。 2017年,杭州楼市正高歌猛进。 温州人一看,屁的城运来袭,不就是咱们20年前玩烂的“控盘炒房”。 走,去互联网之都杭州,搞起来。 过去的10年间,温州人一路小跑,一路转场。 从P2P的行业大地震,转场到币圈的顶级大会,再转场到杭州的城运红利……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,温州已无人谈及“实业兴国”的梦。 我行走在温州的街头,看着街上奔流而过的玛莎拉蒂、AMG和法拉利。 这座城市,还在时不时的提醒我,它过去的荣光。 只是不知,这些奔流而过的人们是否还能回想起—— 30年前,顶着改革压力前行,在工厂里守着机器,在大街上背着产品到处推销的父辈们。 有人说, 币圈的年轻人最喜欢看的书,是李笑来的《通往财富自由之路》。 他们却忘了, 早在30年前,他们的父辈就登上了BBC,讲述中国的“通往富裕之路”。 这些年,我去过很多城市。 从未有一个城市,能像温州这样让我充满唏嘘。 它仿若是一座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博物馆,充满历史碾过的荣光与遗迹。 它发迹于改革开放初期,靠商品匮乏下的制造业,掘到了第一桶金。 它弄潮于改革开放中期,靠城镇化催生的房地产和大生产催生的能源业,绽放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。 它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联网和产业升级,却从未错过炒房、炒币、炒钱、炒煤炭等任何一轮脱实向虚的资本浪潮。 最终,它迷失在虚妄里。 它曾抓了一手烂牌,却打出了让人叫好的奇迹。 继而,又把一手好牌,打的稀烂。 过往的荣光,是它的璀璨背景色,也是它挥之不去的灰色魔咒。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。 这也是中国资本化浪潮的缩影。 专题研究: 万字长文: 螺旋解体: 城市调研: 重庆:| 北京:||| 上海:|| 苏州: 成都: 武汉: 天津: 其他城市: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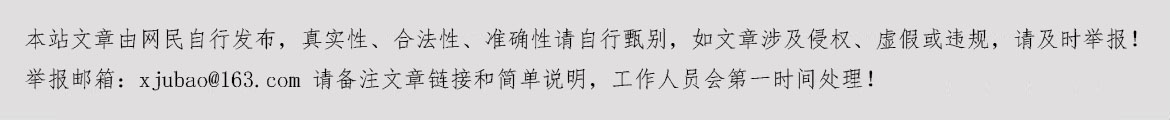
|